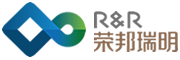
中国改革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地方政府的信用剥离: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剥离;二是央企、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之间信用的剥离。同时还有两次重大的信用建设:一是分税制的改革,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二是国家开发银行推动的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合作。每一次对地方政府信用的剥离和建设,都是一种大的进步。
十八大过后,改革被当作最大的红利,针对未来经济能否以及如何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的讨论和分析很多,但是如何改革却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破解的难题。不让地方政府继续躺在国家的信用簿上,让其成为独立的信用主体是重要的改革,也是当务之急。前二十年的所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城市这个信用主体缺位或越位有关系。
之前论述过地方发展的各种不平衡状态,各地方面临的问题颇有不同。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看各地方的城市发展水平,似乎离民众的理想还有颇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巨大的发展潜力。
要弥补这个空间的不足,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相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城镇化过程,各地方的公共服务设施,属于投资相对落后的领域,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更谈不上为城镇化的未来提供更大的支撑。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好的城镇化一定要转变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局面,这种转变不是说政府不投资了,而是政府的投资要转变领域,转变方式,并引导社会资本一起投资,要投资的方向是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将房地产一头独大转向均衡发展,要补上旧账,还要为未来的城镇化提供牵引。要实现这一点,城市建设领域的投融资体制,仍然是未来需要改革的重点方向。
在前面,我们将过去二十年城镇化的进程,分成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阶段,应该说两个阶段都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引发了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政策出台的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城市建设领域的投融资行为,让我们以此为例来看看政策的目标与影响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十年是以土地协议出让、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导致的城市扩张时期,于2002年前后,被招、拍、挂制度和土地储备政策所终结,第一次调控的出发点在于防止开发商低价和大规模圈地导致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问题,以及协议出让导致腐败和市场不透明问题,其衍生出来的结果是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代表的社会资金,被排除出在土地一级开发和城市建设领域之外,一级市场的土地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为地方政府所垄断。
由于信贷资金向一级土地市场集中,新的市场空白出现,地方政府下属的平台,借助政府信用和土地资源,接手了城市建设投融资的接力棒。但是针对如何把城市建设得更加可持续、配套更加完善、规划实施更加科学的政策并没有太多涉及。
第二个十年中,地方政府的融资扩张和投资冲动,使得地方投融资平台再次成为被打压的对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遏制投资冲动。采用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在以2010国发19号文件为引领的一系列清理文件,主要是从信贷政策角度采用了倒逼的方式,名单制、额度控制成为重要手段。但是从投融资方式上仍然为围绕土地为中心的投融资工作留了口子。
但是这一轮政策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四部委最近发布的162号文件,将土地储备融资再次集中到了土储部门,与城市建设再次划清界限,出发点仍然是控制风险,采用的管理手段变成了层层融资额度控制。
从两轮政策的出台和手段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土地作为城市建设过程中最核心的资本归集点和有价值的资源,走了从市场到地方政府、再到行业管理的逐步收缩过程;二是调控手段上明显表现出自上而下统一调控,由中央代替地方做判断过程,甚至是额度的层层控制,有回归中央统一计划管理的味道;三是所有的政策都是针对信用资源入手的,包括信贷资源、土地资源等,而缺少对城市建设如何搞得更科学的改进。
然而,金融风险本应是分散的,应该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在这种统一的调控手段下,中央应当为地方买单的思维倾向会越来越严重,地方城市发展变成了中央统一的额度分配。
另外的缺陷,来自于投融资资源与城市规划实施的脱节。城镇化的过程,具象到城市建设层面,实际上就是城镇规划的实施过程。当这个过程的核心资源和载体——土地,与城市建设的其他部分相脱离,由区域政府统筹变成行业纵向统筹时,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在中微观层面就更难实现了。
所以未来的城镇化要搞好,真正要防范金融风险,要实现均衡发展,实现城市功能的成熟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更需要公共产品的提前投入。如果反向操作,公共服务滞后于城镇化,未来必将带来公共服务更大的负担。按照现在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如果公共服务继续滞后,带来的影响将比上个世纪后十年严重得多。
反思我国政策的出台,其背景具有一个假设,就是地方政府不是独立的信用主体,因此经常会出现上级一纸文件,把地方的很多实践否定。这个否定过程本身破坏了地方政府与企业、市民、农民等形成的信用和信任关系。比如,前阶段某省政府单方面出台文件,不承认市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协议,就严重地破坏了城市政府已经形成的信用生态。信用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基本没有了创新的冲动和创新能力。城市发展的任何创新,应该建立在如何发挥好市场主体作用的角度,而如果地方政府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有可能随时成为一纸空,谁还敢与地方政府合作。这样的结果是资源分配越来越自上而下,政策调控手段越来越技术化,地方政府也就失去了与市场对接的博弈能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将成为泡影。
我们注意到,当下的中国经济,早已非改革之前的一块铁板,而是早已产生了裂变,以城市为单元,产生出众多的中观层面的经济体。如果说国家是一个人,企业就是细胞,而城市则是身体的组织,承担着中间最核心的功能。我们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要正视城市作为中观层面的经济组织者的角色,不再回避矛盾,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让城市政府正常发挥自身作用和承担责任上来,也就是做实信用主体的角色。
因此,打破近年在围绕城镇化中围绕投融资出台的信用上收的政策思维,让信用资源下沉,让市场能够进入,让政府部门退出投融资的操作层面,回归管理职能。政府回归管标准、管质量,而不是管融资、管计划、管操作,更不能由各个部门来分散操作,避免资源向某些特定部门过度集中,否则区域统筹发展这一美好的愿景只能成为口号,最终必将被条块化所割裂。
换言之,信用的下沉和分散,做实基层信用才能使地方有因地制宜创新的可能性,才有实现风险分散的可能性。
版权所有: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