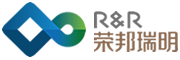
城市建设领域传统的市场力量被排除出去后,谁来作为继任者?应该说与2010年对投融资平台被急刹车式的清理不同,这一次投融资平台替代市场力量成为城镇化投资的主力军,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平稳过渡。
投融资平台来源多元化。如前文所述,投融资平台,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注资成立,承担地方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任务。它常常被被冠以投融资平台的名号,这个称号源自于1992年上海城投的改制。实际上,后来成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公司,前身来源颇为多样化。
一部分公司,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各城市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搞城市建设而设立的建设指挥部或是事业单位,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他们逐渐脱离政府的直接管理序列,转化成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建设实体,尤以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专业公司为多;还有一些政府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能够进行成功的市场化转型之后,也回归到这一队伍。
另一部分公司,脱胎于当年政府搞开发区时成立的大量开发区建设公司,在开发区逐渐向新区、新城转型时,这些开发建设公司也随之成为所在区域的城市投融资平台。
城市投融资平台公司能够发展壮大,依靠的是开发性金融的扶植。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以后,推出开发性金融理念,为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提供长期大规模的贷款支持,但是由于财政不能直接融资的法律限制,国开行要求地方政府在承接贷款时,必须成立一家专门的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统借统还。《开发性金融论纲》和《破解城投公司困局——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基因》中,对平台公司的历史和发展都有描述。正是开发性金融的推动,使得地方政府真正意识到,将资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于城市建设是何等重要,于是各地开始纷纷学习和复制,力求在城市建设融资竞赛中拔得头筹。
与当年市场主导城市建设的胜景在全国遍地开花一样,政府倚赖自己的城市投融资平台为城建输血之所以能够盛行,也完全是资本流向的力量。
“郎顾之争”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其思想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城市建设领域的态度。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逐渐显现,“冰棍理论”不再为人们所广泛认同,争议发展到高潮,就是2004年有名的“郎顾之争”。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如何把国企搞好成为了改革的新方向。应该说,“郎顾之争”所带来的影响,远非终止了国企MBO这么简单,它使得政府的思想意识中,“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词成为了思想深处的一个红灯,甚至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可避免的深深影响了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金融机构的思维。把钱借给国企是最保险的,即使出了风险也不是大问题,国企再烂有政府兜着,这种思想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可谓深入贷款银行之心,甚至时至今日,很多银行仍然奉行这种看起来似乎可以定位成“保守”的经营思路。
对民企不信任思想导致政策上向国资倾斜。这种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的深入城市建设领域,加上过去十年中种种城市病所带来的反思,使得政府将扶持自己的投资主体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这种“信政府”,“政府兜底最保险”的思想氛围下,国开行的开发性金融所带来的,是更为广泛的复制效应。以政府还款承诺函为基础的各种贷款、信托、债券、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涌向了城市投融资平台,各商业银行、券商、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都把政府下属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当成了优质客户来源。
投融资平台公司这个群体本身的示范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群体虽然后来被广为诟病为不够“市场化”,脱离不了政府的干预,但是在政府体系中,可以算得上是颇具有学习精神,并于1999年年由沈阳、上海等几大城投发起,成立了全国城投公司协作联络会,每年召开三次大会,各大城投轮流坐庄,交流经验。最为各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所艳羡的,就是重庆鼎鼎大名的“八大投”,可谓接待考察无数。其以储备土地为融资抵押主要来源的模式,也在各地方的城投公司中广泛复制。
世界性金融危机为国资在城建领域的加强再添了一把火,而给这股城市建设融资大潮添上最大一把火的,是2008年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央行、银监会等发出的一系列政策引导和默许下,迅速集中了巨量的信贷资本。大量城市建设项目立项在短时间内得到批准,城市投融资平台模式也向县一级地区迅速蔓延。
那时,但凡思路比较“活泛”点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干一件事儿——融资,因为谁都清楚,如此宽松的信贷形式,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据悉,全国县一级以上投融资平台,截至2010年,数量达到8000家以上,其中县一级的平台,相当一部分是在08年以后成立的。
那时得意忘形的平台公司和政府,为城市发展埋下了祸根。那一阶段,融资平台的日子可谓相当滋润,只要跟政府签一个回购协议,政府给出一个还款承诺函,贷款或是债券就能颇为容易的到手,尽管投资的大多都是毫无收益或是收益很差的基础设施项目。“白证”(以融资为目的,在征地拆迁案没有进行或完成的条件下,由国土部门为金融机构特办的,不对外使用的土地使用权证)这一如今已经不再被许可的土地储备方式,也在这一时期广泛的被用于抵押物。金融机构们也在忙着给政府出点子,催促政府把下面的平台公司或者进行合并,以做大资产规模,多发债券或是多贷款;或者把历史债务放到老公司里,把干净资产注册成新公司,以创造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再次融资。
这一阶段政府主管城市建设的领导,最乐于讲的三个字就是“不差钱”,在2006年前后还搞得颇有些风生水起的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PPP、BOT等向外资和民资开放来为城市建设融资的模式,在这一阶段基本消失,反正政府不差钱,何必那么费事去招商引资,不如直接去公关银行,把钱弄到自己手里花。
伴随着巨量资本涌入城市建设领域,许多城市也变得像大工地,各种“拆拆市长”“挖挖书记”们可谓一时风头无二。但是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风光的背后也埋下巨大的隐患,在两年的高潮之后,以政府主导、各类城投公司为载体的城市建设高潮,很快随着2010年国发19号文件的出台,迅速陷入冰点。
版权所有: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